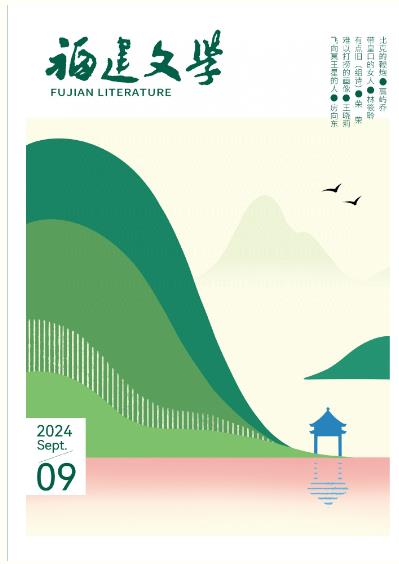 高屿乔这两篇小说中都有一无所有之人。我们仅仅是害怕一无所有,但作者写出了一无所有中引人深思的况味。
高屿乔这两篇小说中都有一无所有之人。我们仅仅是害怕一无所有,但作者写出了一无所有中引人深思的况味。
《比克的鞭炮》里一场矿难改变了人们的命运。矿工父亲的抚恤金为“我”铺开进入城市的路,“我”则把自己的身世和父亲的死永远埋在身后。很多人和“我”一样,唯有傻子比克还坚守在发生矿难的山上,睡在破庙里,吃坟前的祭品,时而清醒时而疯癫。
从世俗的角度看,“我”的选择肯定是正确的,人生很多时候就是要向前看,别回头。但是当比克犯起疯劲,死死攥着“我”的胳膊,说我们都是被钱收买的叛徒,忘了那些死在山里的父辈时,“我”的心却被狠狠刺痛。这刺痛成了故事的起点,“我”和比克的地位也不知不觉间掉转了。正常的心智、城市的工作与生活,老婆和孩子——“我”拥有的一切反而成了累赘,以至于“我”必须远走,必须蒙蔽自己的心;疯癫、一无所有的比克则可以永远留在那座山上,让那仇恨永远停留在心间。
正所谓“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我”与比克的关系透露出一种关于现代都市人的困境。我们拥有的那一点可怜东西,反而让我们失去了选择的自由。难道真有正常人会羡慕比克那样的生活吗?当这种选择的自由象征着一种面对生活的勇气和底气时,我相信有人会羡慕的。
《标记》的主人公程贵林是个一无所有的中年男人,前妻带着儿子改嫁,如今连他给儿子留下的姓氏、煞费苦心取的名字也要一并改掉。因此程贵林才会对自己买的那个电瓶车车位那么在意。钱多钱少只是表象,车究竟停在哪里也不是问题,关键是自己按规矩买的车位为什么不能只属于自己?自己拥有的东西凭什么就要被别人不断践踏、掠夺?
他索性赔上所有空闲时间死守在自己的小车位里,哪怕在炎热的天光下汗流浃背,哪怕被人当成无所事事的怪胎。他觉得自己对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有人误认他是看车的,给他几角一元,他也要煮些绿豆汤还给人家,他不欠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不应该欠他。
然而意外来了,一个骑车的女人拿着程贵林的绿豆汤,单手扶把,转头就被货车碾死。程贵林那朴素的信仰轰然崩塌,他整夜整夜不睡觉,也想不清楚女人的死和自己的绿豆汤有无关系。他意识到从此都别想再和这个世界谈什么两不相欠、一清二楚,他第一次希望那个车位从来没属于过自己。
痛苦中他再次想起前妻和自己离婚的缘由——自己没本事,儿子又有先天性心脏问题,需要一大笔钱来做手术。前妻找到了一个男人为儿子提供手术费,手术很成功,儿子的姓名也即将属于他的新父亲、一位能给他带来幸福的父亲。在电话里程贵林听到儿子的欢声笑语,他突然明白了拥有和责任之间的关系,在自己没有力量承担任何责任的时候,儿子也好、车位也罢,一无所有也不见得是什么坏事。
在《比克的鞭炮》中,一无所有意味着面对选择的勇气。在《标记》中,一无所有意味着面对失去的释然。比克和程贵林是不幸的人吗?就像哲学家爱比克泰德曾经说过的:“我不能逃避死亡,难道我还不能逃避对死亡的惧怕吗?”面对充满偶然性也充满必然性的人生,幸运或不幸也许是个伪命题,面对人生的态度和心境才更重要。高屿乔是2000年出生的青年作家,他的小说有超越年龄的老到,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看透且用文学的方式呈现了许多人一辈子都无法明白的道理。
说到年龄,我是1990年出生,和作者正好相差十岁。现在网上都说五年已可划分一个代际,然而看到“比克”这两个字时,我认为我们仍处在一个代际,至少对于文学来说是这样的。
通过高屿乔的这两篇作品,我们可以重审当下文学创作中的经验与代际问题。比克是日本漫画《龙珠》中的一个重要角色,这部漫画从1984年开始连载,比克第一次出现大概是在1987年,那个时候中国文坛先锋小说风起云涌、新写实小说方兴未艾。《龙珠》的作者鸟山明出生于1955年,和马原、刘恒、莫言、刘震云们正是“同代人”。时间在这里呈现出一种不真实的交错感,这些中国作家已经进入了文学史,成了青年作家仿效的对象;而同时期的比克出现在一位2000年出生的作家笔下,看上去俨然颇为新鲜的元素。
近些年中国的通俗文艺作品,比如《王者荣耀》《原神》《黑神话:悟空》都在海外的青年群体中产生了相当的影响,与最新潮的文化、技术保持着较为紧密的对话关系。但反观纯文学,无论是在写作资源还是在受众群体上都存在着代际方面的“滞后”。对此不少文学研究者、作家不以为意,认为那些通俗作品中的形象与元素对于纯文学呈现深刻的思想、丰富的人性并没有什么太大帮助,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就以《比克的鞭炮》中出现的比克为例。《龙珠》将中国古典和欧美流行融合成了日本风格,而比克则是一个“异质性”因素。它的穿着打扮都类似我们记忆中的阿拉伯人,它的皮肤是穆斯林文化视为神圣的绿色。除此之外,这个形象还有其他的独特设定。它在幼年就被迫从那美克星流浪到地球,不知道自己是“外星人”;它有千百年的寿命,只喝水就能生存;它善良的一半成了地球上的天神,邪恶的一半则要把地球变成炼狱,它常年居住在远离尘世的天上。当《比克的鞭炮》中的那个时而清醒、时而疯癫的人被命名为“比克”时,他在山上餐风饮露、独守父辈隐秘史的行为中,也就有了真正比克身上那种沉重的孤独。
小说对这一外国通俗文化元素的使用,有效增加了与读者共情的可能性。与古诗词中常有的“用典”不同,《龙珠》与比克被无数80后、90后、00后熟知,并非稀有知识。随着更多90后、00后作家走上文坛,在比克背后还有海量可以丰富作品内涵、唤起共情的通俗文化符号。这些符号不仅能让纯文学中的形象和情感变得更具体,也可能会带来新的故事模式与抒情方法。
高屿乔的小说中还暗藏着文学与电影的联系。《标记》中无奈的释然与苦涩的幽默,与钟孟宏导演的《一路顺风》《阳光普照》颇有相似性,尤其是程贵林这个人物似乎与演员陈以文的一部分银幕形象有着强烈的对话关系。程贵林固执地坐在自己的小车位里,用朴素的伦理和逻辑质问这个世界,却遭遇无法承受的生命之重,在这一幕中文学与电影承载的灵韵是打通的。虽然现在很多作家都在为影视化写作,但文学和影视之间的关系更多还是停留在市场和生产的层面,并不像20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样,呈现出艺术上相互影响、激发的明显趋势。在艺术上,文学与影视的交融有广阔的空间,在文学的接受层面这种融合同样重要。小说和影视都是叙事性艺术,两个受众群中“爱屋及乌”很常见,而对于年轻一代来说,很可能他们对故事和文学的兴趣最初来源于画面和影像。因此打通文学与影视的创作,更能吸引他们的共鸣。
上面似乎谈了一些文学之外的内容,这是高屿乔的小说带给我的一些思考。这种发散式思考的基础,其实还是两篇作品在文学层面的扎实,小说中那些无处不在的叙事、抒情、比喻、象征都相当老到。就让我以对高屿乔笔下的一句话的细读作为这篇文章的结尾。
那是我第一次见他母亲打比克,在那条跟咽喉似的狭窄的巷子,我以为世上最凄厉的哭声不过如此,一个知晓真相的母亲抽打着或许会永远沉浸在梦里的孩子。(《比克的鞭炮》)
那条巷子与比克的喉咙叠加在一起,空间的狭窄和生活的匮乏也叠加在一起,而哭声就从这个双层空间中逼迫出来传到每一个人的耳朵里,作者非常精到地用一个句子完成了空间和听觉这两个层面的事情。“知晓真相”的母亲抽打“沉浸在梦里”的比克,肉体层面,前者是强势的施动者,后者是被动的承担者,但精神层面,前者才是痛苦的,后者则是因为懵懂而平静的。有了前面的铺垫,这里一个句子就完成了肉体和精神层面的叙事任务。在这短短的六十多字中,高屿乔藏了多个层次、多重反差。类似这样的句子,在高屿乔的小说中只是寻常,相信有这么扎实的文学功底作为基础,那些文学之外的东西一定可以锦上添花,让他的文学世界结出更多奇异、鲜美的果实。
责任编辑 林东涵
(《福建文学》2024年9期 [5816])

